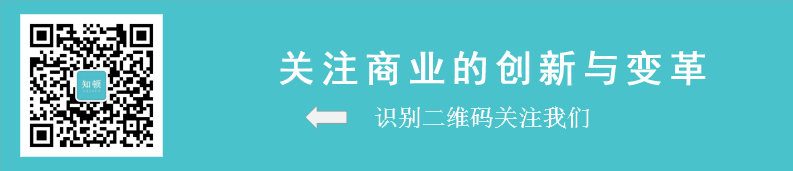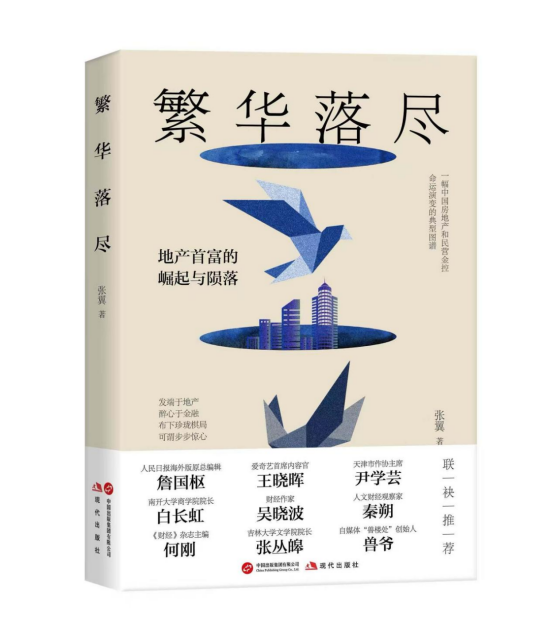
张翼: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曾任知名财经媒体首席记者、房地产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著有《柔韧有“俞”》《微波炉战争》《繁华落尽》等8本书籍。
“这100本书,真是幸福的烦恼。”结束采访两天之后,财经作家张翼给记者发来一张照片:几大摞书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办公桌上,正是他的新作《繁华落尽》。
这些书的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故事。前不久,张翼在上海书城举办新书签售会,热情的读者将《繁华落尽》抢购一空。签售会临近结束,面容姣好的女性读者王苍德走到他面前,眼中闪烁着真诚:“我曾经也是地产行业的从业者,这本书给我很大触动,也道尽了我们这代人的荣光与遗憾。在时代浪潮的回忆录中,仿佛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曾经的我们。”她要买100本《繁华落尽》赠给同事和朋友,但因书店库存告急,便跟张翼商量,自己网购,寄给张翼签名,再转寄给她。张翼感慨:“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认可,这份热忱值得珍惜,我一定会认真签好。”
《繁华落尽》以犀利的笔触与深刻的洞察,将房地产行业的风云变幻、兴衰沉浮展现在读者面前。自今年5月出版以来,在各大销量榜上名列前茅,持续引发了市场热潮。张翼曾是知名财经媒体首席记者,长期聚焦地产、金融领域,后又转型为知名房地产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亲历了行业的黄金时代与跌宕起伏。从媒体人到地产从业者,再到如今用笔墨剖析行业内幕的作家,张翼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张翼的世界。
读报告文学迷上写作 采访诸多成功企业家
1975年,张翼出生在山西省夏县,7岁随军,在部队大院生活。父亲是空军政工干部,也是天津一位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他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张翼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读物,是父亲常带回家的《报告文学》杂志。他在《1987报告文学选》上读到贾鲁生的文章《丐帮漂流记》。“我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完的,觉得太神奇了,原来还能这样写故事。”多年后提起这部作品,张翼依然动容,“作家混迹丐帮数月完成的这篇体验式作品,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可以如此有力地呈现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广播剧《平凡的世界》,李野墨的磁性嗓音让全国听众准时守候,张翼也是其中之一。路遥和《平凡的世界》成为对他影响最深的作家和作品。“这部小说我买过五个版本,上大学后仍时不时地重读,其中有几本翻烂了也舍不得丢。”他说。
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张翼加入了校大学生通讯社,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撰写人物专访。时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乔迈的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被改编为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曾红遍大江南北。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张翼和同学魏春桥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吉林省作协,拜访乔迈。
“那天下午,乔迈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我们聊了很多,叮嘱我们一定要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这句话成为指引我创作的灯塔。”张翼回忆,不久后他采访了古文字学家吴振武教授,写出万字报道,刊发在《长春晚报》上,成为他写作生涯的第一个亮点。
2001年,身为财经记者的张翼开启了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家的独特观察视角。他先后采访了数百位商界人物,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见证了企业的兴衰,更让他开始思考商业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张翼接触过的众多企业家中,柳传志给他的影响尤为深刻。“柳总常说一句话,‘把嘴皮子磨热’,其实就是强调深度沟通的重要性,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他对柳传志的“践诺守时”非常钦佩,无论遇上风霜雨雪,无论参加会议还是接受访谈,柳传志始终保持提前15分钟到场的习惯。这让张翼意识到,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把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做到了极致。
在中国科技会堂参加的一次座谈会,是张翼观察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走出巨人集团破产阴霾的史玉柱一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看上去史玉柱显得平静、理性,他仔细分析自己失败原因的神态,与张翼想象中的落魄企业家截然不同。“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深刻的。史玉柱像解剖标本一样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大败局,直面失败的勇气让我震撼。”这次采访后,张翼开始关注商业故事的另一面——在成功学盛行的年代,那些失败的教训,往往蕴含着更珍贵的智慧。
2011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处于高峰期,张翼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媒体工作的经验让他感到: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商业、企业家到底在想什么,仅靠外部记录远远不够。他转型成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亲历了土地拍卖的疯狂竞逐,见证了商业谈判的暗流涌动,也体会了政策调控下行业的剧烈震荡。“以前写企业家故事时,我记录的是他们展现给媒体的样子;改变身份后,我能听见会议室里没说完的后半句话、看到合同背后没写明的潜台词。”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商业报道中最稀缺的内部视角。
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现实的影子
读过《繁华落尽》并了解张翼的人会发现,在小说中上市房企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李心远的身上,有很多张翼的影子。“我承认,小说中李心远的原型就是我。这个人物身上藏着我从媒体人转型经理人的全部印记。”张翼直言,有朋友看完小说后发来微信说,很喜欢刚正不阿的“铁皮核桃”李心远,这样的读后感让他颇感欣慰。
张翼回忆十几年前的自己,走进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时,不知道未来会把那些糗事——初入职场的手足无措、卷入权力斗争的身不由己,以及在高压环境中“穿着小鞋跳舞”的内心挣扎都写进小说。“李心远是理想版的我。”张翼笑着说,“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地产人的迷失与回归、坚守与秉持、成长与蜕变,这个人物形象有助于建立并达成读者对年轻打工人的共情预期。”
2019年5月,河北卓达集团实际控制人杨卓舒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的消息让张翼感到震惊,也由此萌生了记录地产首富群像的念头。这些地产商从风光无限到黯然落幕,都有一定的相似性:欲望膨胀、认知陷阱,以及对金融杠杆的危险迷恋。
《繁华落尽》中惊心动魄的情节,藏着太多房地产圈的真实故事:李心远接受总裁易安面试,是张翼当年求职的情景再现;易安被突然替换的剧情,也有现实原型——一天深夜,张翼和同事们都收到了“明早集体乘车到郊区开会”的通知,第二天大会宣布“总裁因个人原因离职”,全场人都蒙了。
书中每个人物都有现实的影子。地产首富王胜伟融合了多位企业家的特质,既有“打造好房子”的专业精神,也有在金融扩张中迷失的冲动;而那位敢在公开场合怒斥地产商,预言企业五年之内要暴雷的“河东省人大常委”朱可臻,原型则是被称为“夏青天”的夏家骏先生。
“夏老2021年去世,生前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他穿着朴素,甚至不修边幅。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还曾被拦在门外,只因看起来不像大人物。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纯朴、平和风趣、倔强执着的老人,一旦较起真儿来,敢碰硬、有韧劲,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成了百姓心中的‘夏青天’。”张翼特意在书中保留了夏家骏“布衣委员”的特质,让朱可臻这个人物成为刺破浮华的一把利剑。
创作《繁华落尽》的五年,是张翼在纪实与虚构间较劲的五年。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他坦言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第一稿写得像新闻报道,虽然公司和老板的名字都改了,但情节却写实到吓人。他请当年的领导过目,领导调侃说:“你这么写会惹麻烦,小说要写得面目全非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才有意思。”张翼接受建议,把故事打碎重组,用事实做骨架,以文学做血肉,既让圈内人看出门道,又不会对号入座,最终才有了这部35万字的作品。
有人劝张翼,当高管不是挺好吗,何必“不务正业”写小说。但张翼深知自己的内心想要坚持的是什么。那段日子,他总翻看卷了边的《平凡的世界》。“当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很多评论家表示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直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被广大听众听到,才引发了巨大反响。路遥用作品回击了批评他的声音,我也想用作品证明自己。”张翼说。
《繁华落尽》的出版过程也十分艰难。2023年完稿后,张翼联系了二十多家出版社,编辑都摇头,说题材太敏感。后来他终于成功与一家出版社签约,八个月后,完成了三审三校、制作了封面,但最后一刻被叫停了。
小说热度突破地产圈 想再写一本家族往事
2024年7月,张翼与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他终于可以像路遥那样,用坚忍来证明文字的力量——不是为回击质疑,而是不辜负自己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
出版后不久,这本书的热度突破地产圈,连张翼所在的家长群也开始讨论。“有人在谈论我的这本书,说她看到凌晨两点,上班路上还在翻。群里的家长都很有兴趣,有人当天就下了单。”这种跨圈层的共鸣让张翼感到意外,同时也很惊喜,“后来我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房地产行业和每个家庭的财富、生活都息息相关。”如今,《繁华落尽》的影视化改编也已提上日程。
现在的张翼已投身新的领域,作为企业高管开疆拓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标准的“斜杠中年”,白天是职场人,晚上是写作者。双重身份的切换对他来讲并非负担,反而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他计划60岁之前完成一部记录父辈追梦历程的非虚构作品,这个想法源于家族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末,张翼的父亲调到驻津部队任职,全家人也迁居武清。天津作为张翼的第二故乡,不仅承载了他的成长记忆,也见证着一个家族写作梦的追寻与圆满。他的大伯虽然终生务农,但一直怀揣作家梦,曾在1960年慕名拜访山西著名作家、与马烽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西戎,西戎给他题字:“提高思想水平,提高艺术表现能力,努力创作。”这幅字至今仍留存在山西老宅。二伯是当地知名书法家,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备受称赞。父亲在军旅生涯中也一直笔耕不辍,最终实现了作家梦。张翼想把家族往事写下来,传承给后代。
“写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张翼说,他始终相信,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抒写,因为那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生动注脚。
引领读者走进故事 是小说的终极使命
记者:小说创作在揭示真相的同时,如何避免标签化?
张翼:就像我年少时读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他笔下的丐帮群体,绝非简单的乞丐标签所能概括,而是有血有肉、有挣扎有算计的鲜活个体。其实,地产商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复杂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被放大了。创作这部小说时,我特意保留了不可知论空间,在关键处留白。小说结尾那个非婚生子回来争夺财产的开放式情节,就取材于多个地产家族的真实纠葛。我不想给出答案,就像当年乔迈先生教导我的,要让读者自己走进故事里。小说的终极使命,不是用新标签替代旧标签,而是打破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认知窠臼。真正的反标签化,是让读者合上书后一声叹息:“换作是我,又当如何?”
记者:从财经记者到地产经理人,再到作家,你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伴随着对行业的深入理解。如果让你以现在的视角,重新审视做记者时的新闻报道,会对自己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张翼:或许我会少一些简单的批判,多一些理性的建言。当年我写过一些企业的批评报道,觉得自己揭露了真相,很有成就感。当时就有企业的品牌公关负责人跟我说:“张老师,哪天你也进了企业,就能理解我们了。”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直到真正进了地产公司,才有更深的体会。做记者时我总想搞个大新闻,如果重来,我会多些耐心,像我父亲那样,沉下去聆听、记录更多的故事,不只写发生了什么,更写为什么会这样。
记者:你认为《繁华落尽》这部小说的价值是在于记录还是反思?是否担心被过度解读?
张翼:记录与反思,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本质上,这部小说是用文学的“手术刀”给时代的“病灶”做手术,以记录来保存标本,靠反思来进行诊断。无记录,反思则无价值;无反思,记录则无意义。我始终警惕作品沦为道德审判的工具,为此在创作过程中构建了两个防护网。首先是把个体悲剧升维至时代特性,正如企业家张瑞敏所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在小说里,地产商王胜伟这个人物是多位地产商集体形象的投射,因此,他的困境也是集体的,而非个体。其次是用人性复杂体来抵抗标签化,王胜伟体现出多个侧面,比如他创业早期的俭朴生活,吃烧烤的蘸料都要喝掉,后来却生活豪奢,再比如他对爱人、情人温情脉脉,面临抉择时却又决绝、冷酷。我想揭示出一个真相:善恶从来不是商业精英的单选题,而是时代交由他们作答的论述题。
(本文来源:天津日报作者:田莹)